[bs-quote quote=”我們與精神疾病,究竟有多少距離?還是,正因為刻意與之保持距離,才醞釀成衝突?” style=”default” align=”center”][/bs-quote]
二○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九點,高等法院臺中分院(臺中高分院)刑事庭內,在經過朗讀具結文並簽名後,衛福部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何儀峰坐在法庭正中心,面對三位法官,左側是被告賴亞生及兩位律師,右側是負責起訴的檢察官,以專家證人的身份,針對被告精神鑑定的結果接受交叉詰問。
一年多前,賴亞生因氣憤牙醫診所聯合起來隱瞞妹妹行蹤,闖進診所持刀砍殺素不相識的診所人員,導致兩位女性員工分別受到輕重傷,牙醫師王冠中被害身亡,經過臺中地方法院審理,認為其犯行嚴重,手段兇殘,但經鑑定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,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減刑規定,依法不得判處死刑,於一審判處無期徒刑。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減輕其刑的依據,就是何儀峰的鑑定報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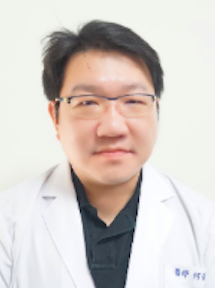
圖片來源:截自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官網。
從被告思覺失調症病史、案發當天行為的辨識與控制能力、被捕後接受偵訊時的反應、精神鑑定的流程,二審法庭裡的整場詰問,幾乎全由檢察官掌控,對鑑定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。
「就我們看這件事,會覺得他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殺人意圖,比較像是不小心傷害致死這樣的概念⋯⋯」程序進行到一個半小時的時候,何儀峰突然說出的這句話,令底下的旁聽民眾與被害者家屬一片譁然,噓聲此起彼落。
在場的人們,從法官、檢察官,到民眾與受害者家屬,難以理解,一死兩傷罪證確鑿,怎麼是一句「不小心」可以帶過的?
隨著連續數年社會重大案件嫌犯疑似有精神障礙,司法精神鑑定逐漸成為各方議論的焦點,在臺中高分院的這個騷動,具體而微展現司法與精神醫學、一般大眾與精神病患之間的扞格。
其中,最難以跨越的距離,就是直觀上賴亞生明明看起很「正常」,並不像小燈泡案的王景玉活在荒謬的幻想中,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。

一審判決書中,詳細比對各方說詞,還有監視器影像佐證,賴亞生坦承起訴書的客觀事實,對於犯行也認罪,他於警訊中供稱:「我與受害者是沒有仇恨或糾紛,但是我打電話到診所要找我妹妹時,診所同事會幫忙隱瞞告知我賴麗茜(其妹)都沒有上班該情事,會讓我白跑好幾趟,導致我對賴麗茜同事不滿,我會朝⋯⋯頸部刺殺他們,是因為當時他們都會幫忙掩護我妹妹賴立茜行蹤,我想要殺死診所全部員工,我清楚刺殺頸部動作是會導致人員死亡⋯⋯」
當天他由大樓警衛口中問出妹妹其實有來上班,證實同事的掩蓋欺瞞,接著上樓對櫃檯小姐佯稱要拿東西給妹妹,從背包取出折疊刀,乘其不備持刀猛刺,慘叫聲驚動其他人出來查看,接連刺傷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員與奮勇上前的牙醫師,接著敲廁所的門,待躲藏其內的工作人員開門,讓他確認妹妹並沒有在裡面,就此停手,並在警察趕到當下,不願棄刀,期待在衝突中使警方開槍,達到結束自己生命的目的。然而,在辣椒水的噴射下,他的眼睛瞬間睜不開,刀從手上掉落,趴下就逮。

圖片來源:Pixabay/作者:Brett_Hondow
檢察官強調,被告可以先跟門口警衛探查妹妹的確在診所內,等待時機才從包包裡抽刀砍人,且並非不由分說亂砍一通,當發現廁所裡沒有其妹行蹤,其內工作人員也未展現阻擋姿態時,停止攻擊行為。整個過程可以看到,從刺殺的動機、時間與地點,被告皆能選擇、等待與判斷,在事後的偵訊期間,也能清楚回覆問題、交代犯案過程,並沒有出現幻聽幻覺、自言自語等「正性」症狀,表達與理解能力幾與常人無異。
言下之意,鑑定報告所稱賴亞生受「妄想型思覺失調症」影響其辨識與控制能力,顯然是說不通的,被告犯案當時就是一個正常人,該為其殺人及傷害罪行付上完全責任。且由被告病歷顯示,從二○一○年到二○一五年維新醫院開立的抗精神病藥物:氯氮平(Clozapine)劑量只有二十五毫克,且到了二○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就已停藥,醫師建議「支持性心理治療」,至案發當時已兩年多沒有吃藥,其身障手冊也被註銷,顯見其病情穩定,甚至還可以出國打工度假,這不大可能是一名嚴重精神病患可為。

「這邊有個陷阱,Clozapine 的副作用很大,會造成癲癇和白血球下降,雖然劑量偏低,但會使用這個藥,大概是最後一線的選擇;而身障手冊的取消也不一定代表病情好轉,對很多病人來講這還是一個標籤,可能怕受歧視或對就業有影響而放棄申請;而據我了解,被告因為疾病幾乎沒辦法有穩定長期的工作,出國是家裡提供並非自己能力,並與老闆衝突、出現妄想,品質跟內容都很有問題,並不能算是一個工作。」
何儀峰以專業意見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,並一再重申他的鑑定結論,依據被告近十年來的病歷資料以及面對面的會談過程,賴亞生對人事物的關聯性容易產生扭曲解讀、邏輯性與現實感差、想法固執,以致驟下結論,有將妄想變成行動的傾向,而其妄想的核心就是妺妹。

從要當點傳師跟希望妹妹回家,以及對妹妹的憤怒到要殺掉她,陳述的原因跟憤怒程度兩者並不相等,中間的跳躍已經超出常理,但當沒有觸及與妹妹相關的議題,片段的行為包括知道刀要藏起來、誘騙被害人、描述計畫細節的能力皆未脫離現實,但動機的起源:對妹妹的憤怒,是他固著的核心,不滿的情緒逐步累積滲透到妄想裡,以致於要拿刀教訓掩藏其行蹤者。
儘管何儀峰試圖用盡量淺顯的方式,說明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的特質,不易一下子就能從外觀察覺,不像其他的退化型、僵化型等類型,可以明顯從自言自語或呆滯的表情辨識出來,但整場近三小時的詰問過程中,除了檢察官懷疑鑑定結論背後的依據、法官對其解釋直接表示「聽不懂」、旁聽民眾為其陳述時而發出的訕笑與騷動⋯⋯整個法庭對司法精神鑑定的不理解與不信任昭然若揭,何儀峰只能坦言精神鑑定的限制,在案發後經過數個月回推被告當時的精神狀態,一定有其極限。
本文摘自《成為一個新人: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》一書。
[taronews-styles book_title=”成為一個新人: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” book_author=”張子午” book_publisher=”衛城出版 ” book_publish_date=”2019/11/27″ book_cover=”https://cdn.taronews.tw/files/2020/01/2020-01-131.58.01.png” book_link=”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assp.php/taronews/products/0010840558?sloc=main&utm_source=taronews&utm_medium=ap-books&utm_content=recommend&utm_campaign=ap-202001″ book_link_text=”博客來購書” ext_link_1=”https://www.taaze.tw/apredir.html?155785702/https://www.taaze.tw/goods/11100892609.html?” ext_link_text_1=”讀冊生活購書” style=”book”][/taronews-styles]

評論被關閉。